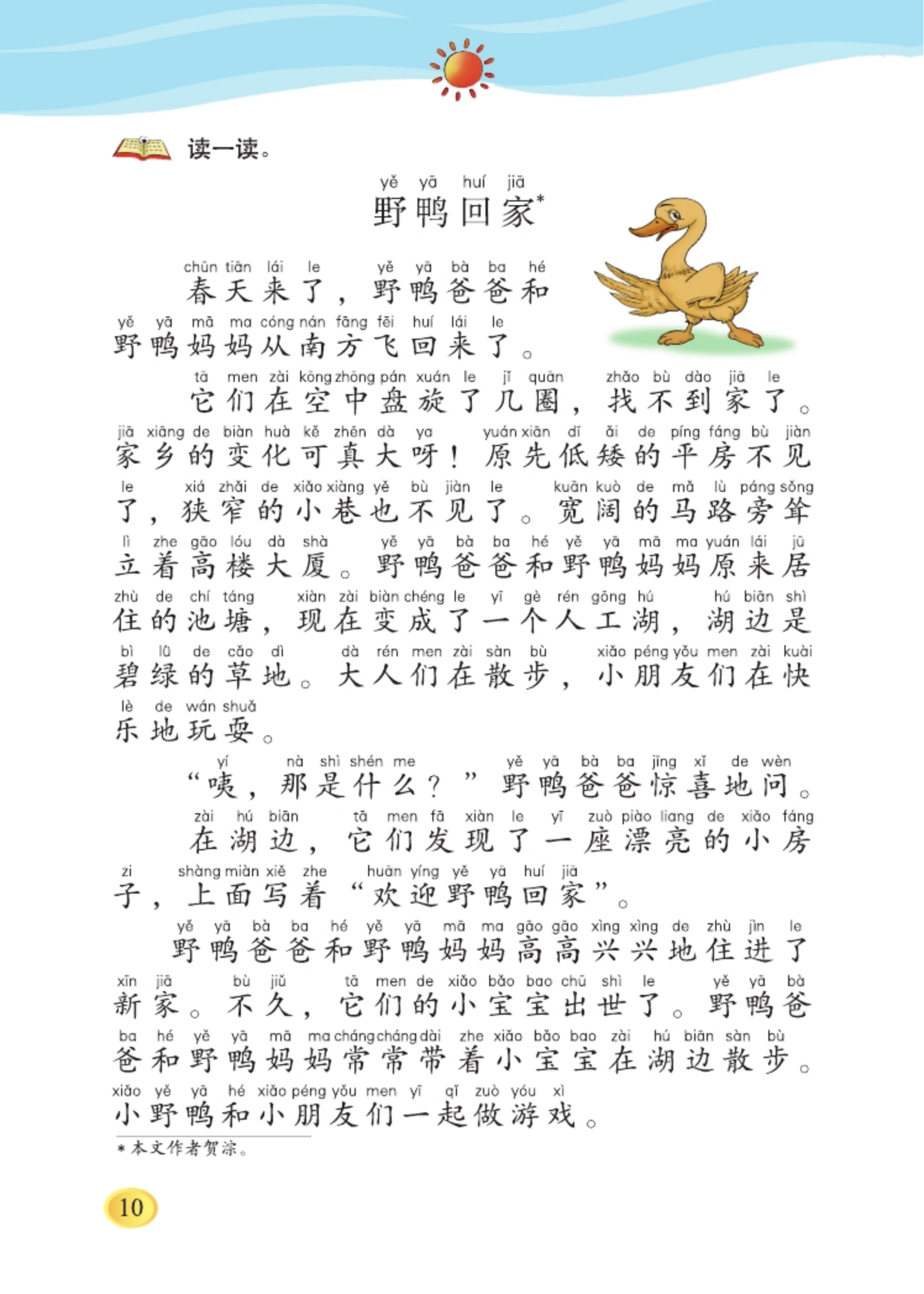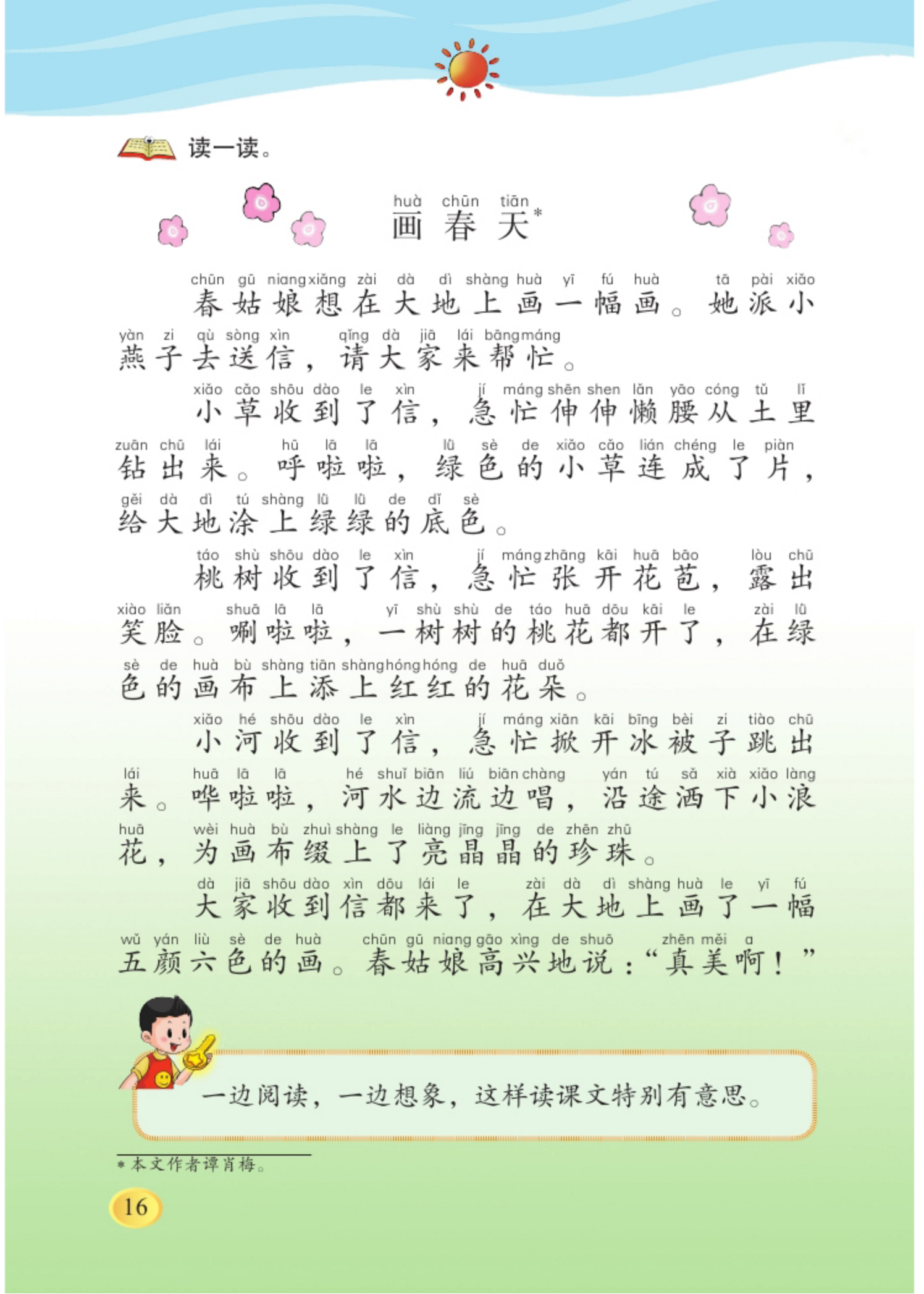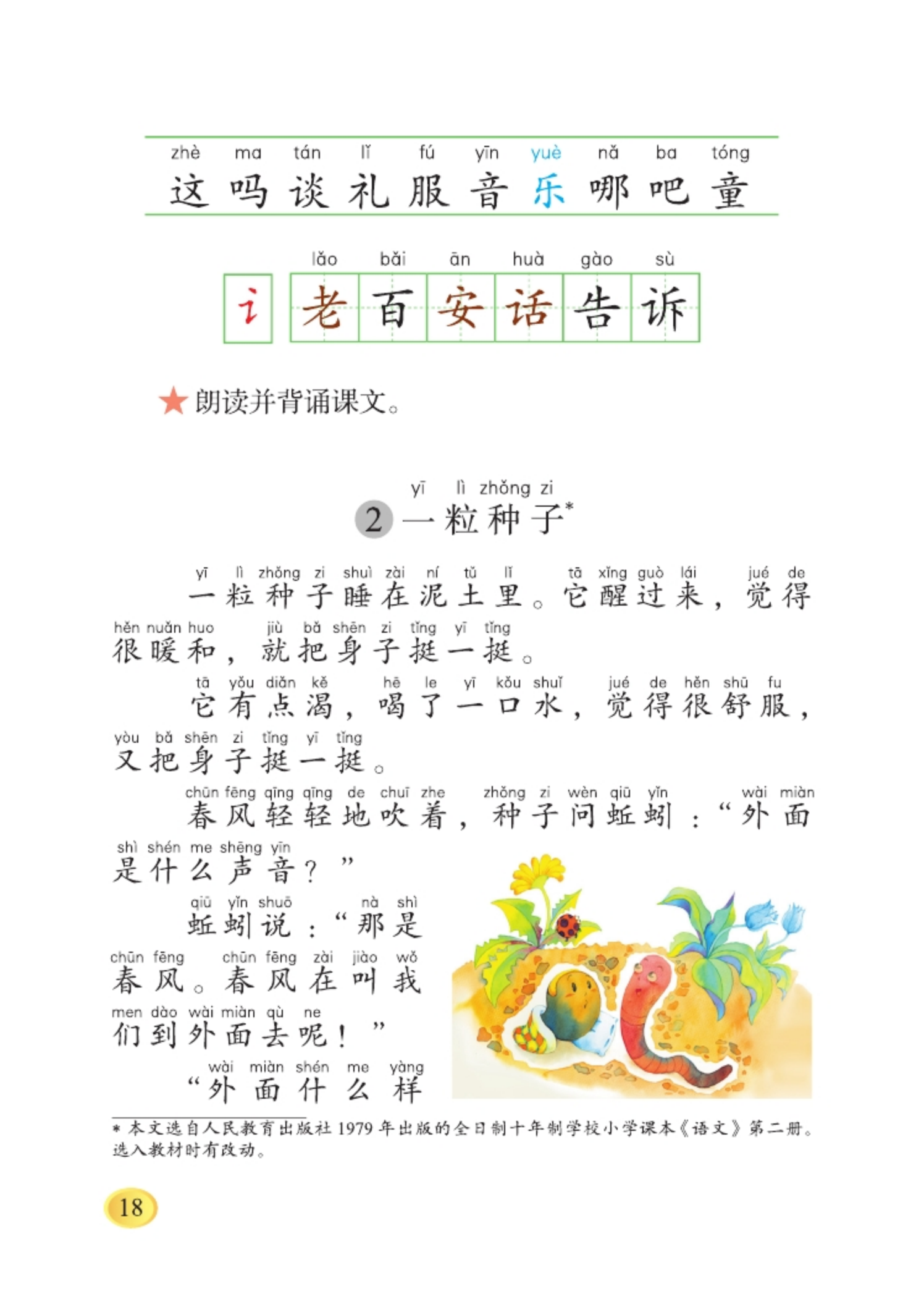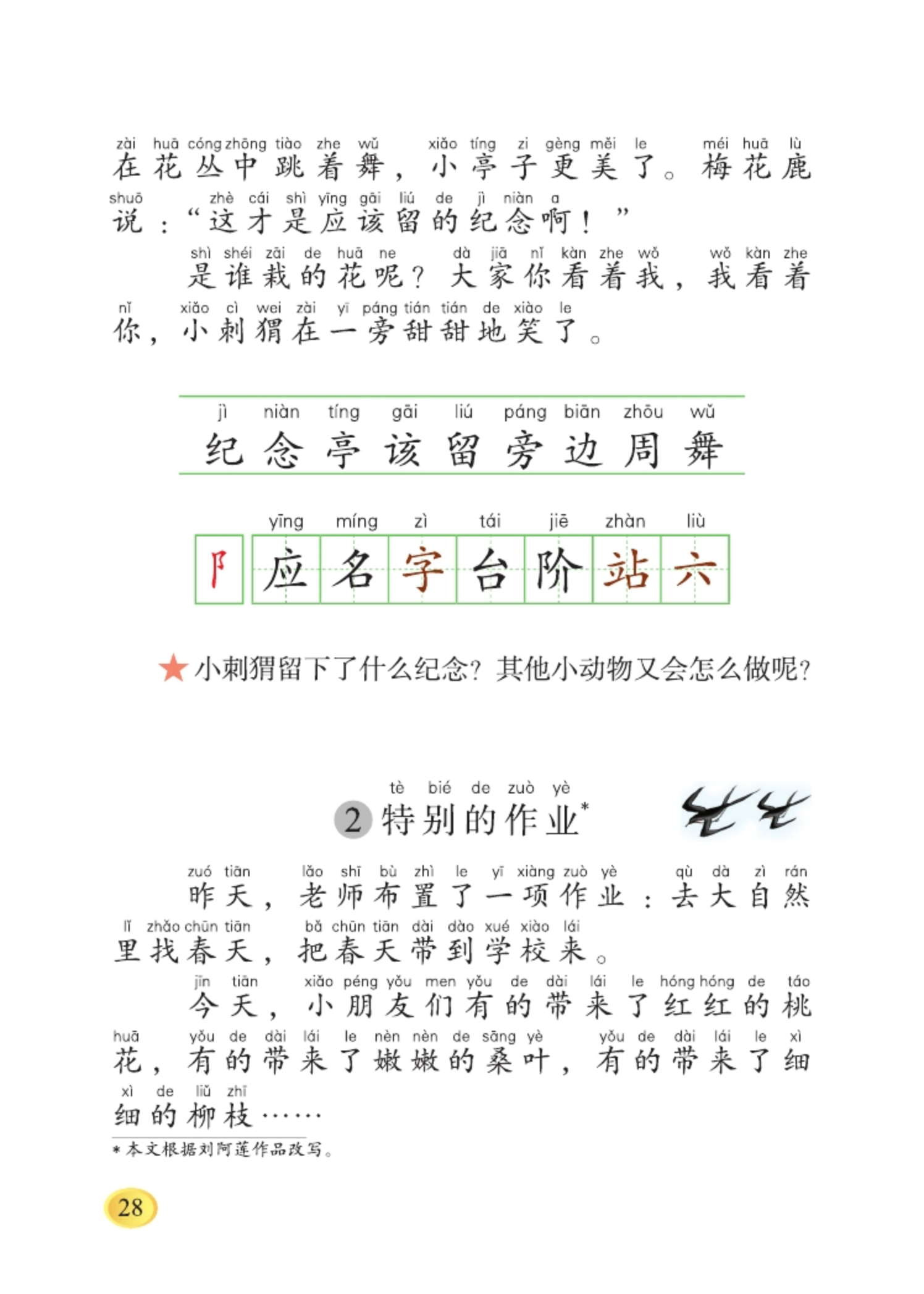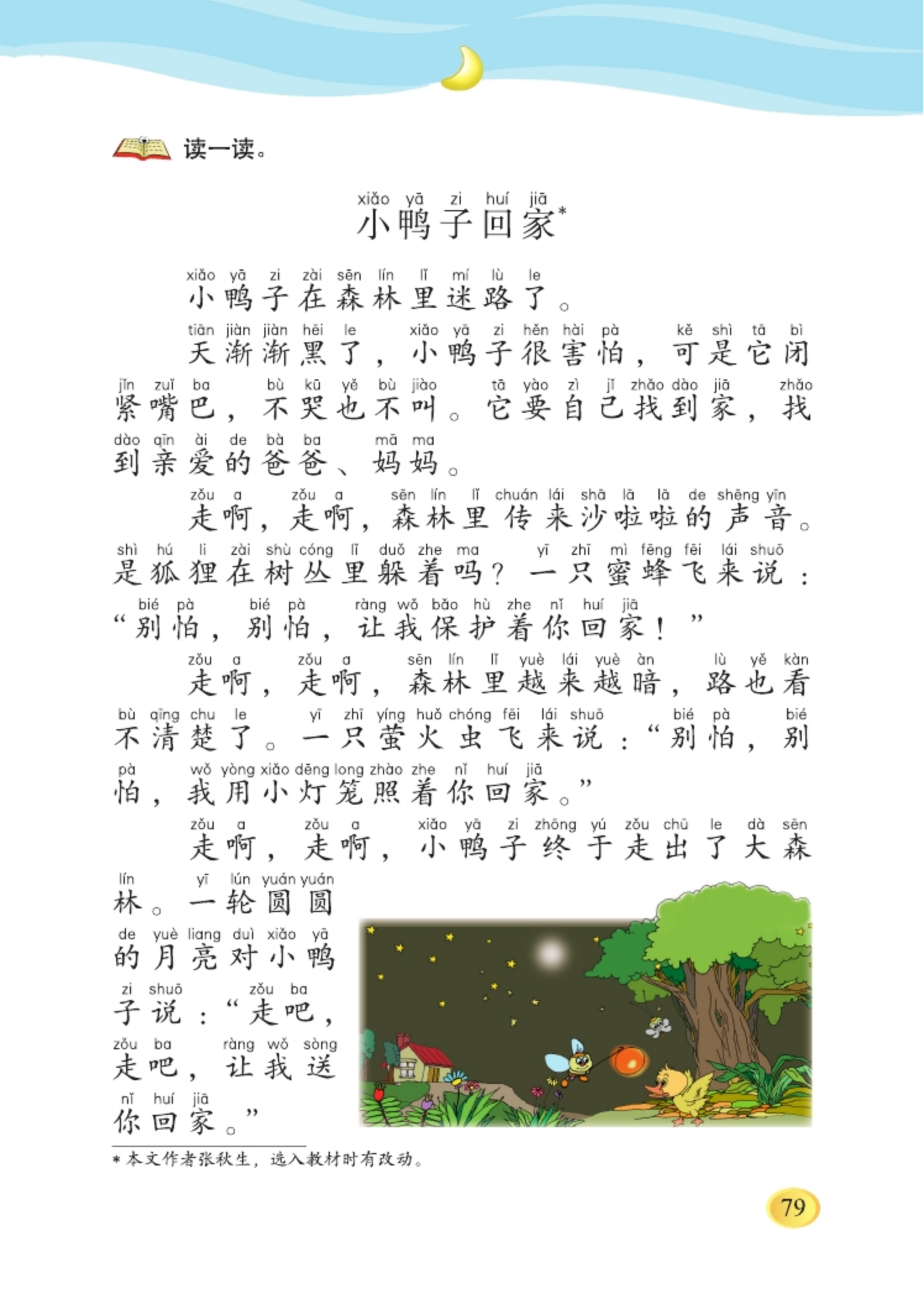北师大版 | 语文 | 一年级下册

当我翻开这本布纹封面的旧书时,细小的尘埃在阳光中旋舞,像无数颗未及落地的文字。牛皮纸扉页上洇开的咖啡渍,是十年前某个春日下午留下的时间标本。手指抚过微微发脆的书页,绸缎般的触感裹挟着油墨特有的醇香漫上鼻尖,恍惚间竟嗅到了泥土翻新的潮湿气息。 封面上那个头戴草帽的男孩正弓着背,将一株青翠的树苗小心地放进土坑。他的红领巾被春风掀起一角,远处山峦的墨线在雾霭中晕染,让我想起外婆总用赭石色毛线勾边的蓝布围裙。那时节总在清明前后,外公会扛着锈迹斑斑的锄头,领我穿过缀满婆婆纳的田埂。新翻的泥土在锄头下翻滚出油亮的波浪,蚯蚓蜷曲着粉红的身躯,田螺壳在沟渠里泛着青灰色的光。 "丫头,种子要像放鸡蛋似的轻拿轻放。"外公布满茧子的手掌托着几粒玉米种,掌纹里嵌着的黑土簌簌落在我的小花布鞋上。外婆提着竹篮跟在后面,篮里的红薯苗还沾着晨露,她总说这是"沾了月亮的灵气"。当我的小铲子掘歪了田垄,外公就蹲下来,用他缺了口的烟斗在地上划出笔直的线,"庄稼人写的字,要叫雨水读得顺畅"。 暮色降临时,远处的泡桐树会垂下淡紫色的铃铛。外婆撩起衣襟擦汗,从蓝布围裙兜里掏出用荷叶包着的艾草团子。蝉鸣声里,外公教我辨认刚冒头的秧苗:"豆瓣菜两瓣叶像蝴蝶翅膀,苋菜的芽尖总爱顶着露珠帽子。"那些浸润着汗水的农耕智慧,如今竟与书页间的光合作用示意图重叠成奇妙的光斑。 合上书时,夕阳正给窗台上的绿萝镀上金边。恍惚看见那年插在田头的枯树枝,不知何时已长成亭亭如盖的模样。风穿过楼宇间的缝隙,捎来几不可闻的稻花香——或许那是二十年前落在书页间的,某粒被遗忘的野燕麦种子,正在字里行间悄悄抽穗。

暮色初合时,老街的青砖缝里已渗出暖黄的光晕。竹骨宣纸灯笼在檐角次第亮起,细雪落在彩绘的嫦娥奔月图上,洇开几朵透明的冰花。巷口卖糖画的老人将铜勺往青石板上轻轻一叩,糖稀流淌的金线便勾住了最后一缕暮紫天光。 书包里新发的课本还带着油墨的潮气,《元宵节》的铅字在路灯下泛着青蓝。我望着扉页插画里穿棉袍的孩童,他们举着的莲花灯竟与橱窗里的电子灯笼重叠——那些会唱歌的塑料兔子正眨着七彩眼睛,可父亲总说纸糊的走马灯才看得见风的形状。 "小心烫着。"母亲掀开蒸笼,团团圆圆的白玉珠在热气中浮沉。糯米香裹着桂花蜜渗进木纹桌缝,让我想起除夕夜祖父亲手写的春联。他总把"福"字倒贴在米缸上,苍劲的笔锋里藏着麦穗的弧度:"仓廪实才能灯笼明啊。" 窗外的烟花突然绽成漫天火树,瞬间照亮邻家妹妹新袄上的盘花扣。她腕间叮咚作响的银镯,与插画里孩童戴的长命锁在火光中交相辉映。父亲往我碗里添了勺酒酿,醪糟的醇香漫过舌尖时,我忽然懂得课本上那句"火树银花合"原是有温度的。 河灯顺水漂远的刹那,对岸升起盏盏孔明灯。外婆曾说这些飘摇的光点是人间寄给月亮的信笺,此刻它们正掠过新建的玻璃幕墙,在霓虹中辟出一条暖黄的星河。母亲指着手机里除夕守岁的照片:虚拟烟花在屏幕上绽放,而祖父的藤椅永远空在团圆饭桌旁。 "来写心愿笺。"父亲递来裁好的红纸,他的白发在灯笼映照下宛如落雪。我摸着课本里夹的压岁钱——崭新的纸币上,拓印着航天器的暗纹。当墨笔悬在纸面时,窗外的许愿灯忽然集体转向,仿佛被某个来自未来的引力轻轻牵动。 零点的钟声撞碎冰棱,电子灯笼与纸灯在雪夜里明明灭灭。课本里的元宵古诗正在智能手表上滚动播放,而我的手心还攥着祖父留下的青铜钱。当跨江大桥的灯光秀点亮天际时,我忽然看见时光的河面上,古老的年轮正生长出新的涟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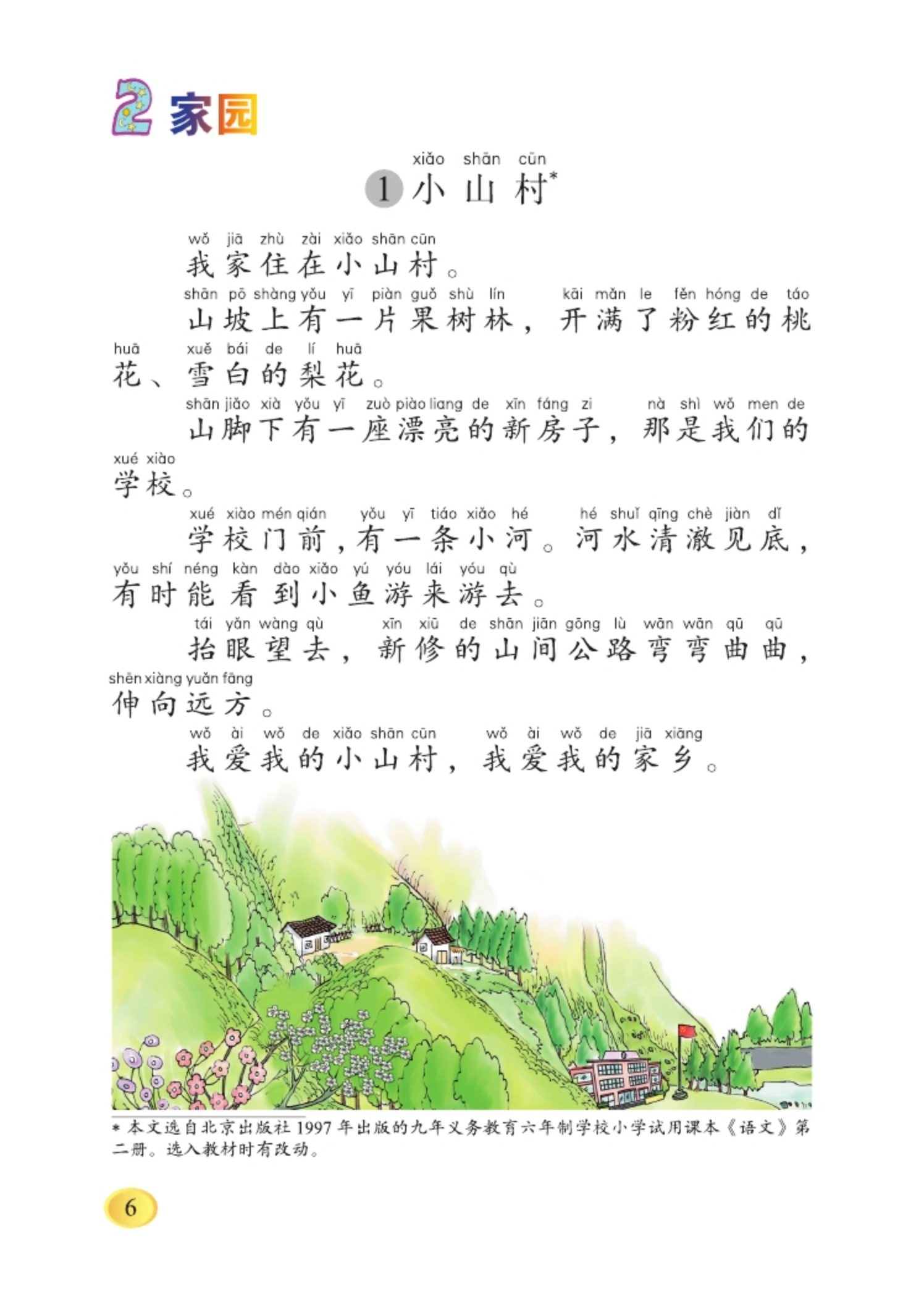

行李箱滚过地铁站瓷砖时,碾碎了最后一片山雾。钢筋森林的玻璃幕墙上,倒映着老槐树蜷曲的枝桠——那是我昨夜用指甲在起雾的窗上画下的图腾。新买的西装口袋里,母亲塞进的艾草香囊正与打印墨盒争夺呼吸权,暗绿叶片间渗出的苦香,总让我想起晒谷场石缝里倔强的青蒿。
出租屋空调外机滴落的水珠,在防盗窗上敲出采茶调的节拍。视频通话时,父亲总把镜头对准檐角褪色的八卦镜,那上面还缠着我离家时断线的风筝尾巴。"昨儿暴雨冲垮了晒场东头,"他的声音裹着电流声,"你刻在青石板上的棋盘倒越发清楚了。"
江南梅雨季的傍晚,我会在便利店的落地窗前看霓虹灯坠入积水。那些破碎的光斑总幻化成水乡歌谣里的菱角舟,乌篷船头晾晒的蓝印花布,此刻正在某座商业综合体的LED屏上循环展播。新同事笑我总把咖啡喝成青瓷盏的姿势,他们不知道我舌尖始终悬着老井水的回甘。
地铁穿过江底隧道的轰鸣里,我听见石拱桥下捣衣的棒槌声。手机备忘录里躺着房东的缴费通知,最新一条却是母亲发来的语音:"后山野柿红透了,给你晒的柿饼吊在西厢房。"当加班到凌晨三点,保温杯底沉着的枸杞突然像极了晒秋时的辣椒碎。
立冬那日收到故乡寄来的包裹,竹编礼盒里躺着十二枚土鸡蛋。我用公司碎纸机里的纸条絮了个窝,蛋壳上的褐色斑点竟与老屋墙根的雨渍惊人相似。主管经过时笑问这是什么行为艺术,我望着孵化器般的电脑主机说:"在养一窝会下金蛋的母鸡。"
年关抢票时,朋友圈开始疯传拆迁公告的照片。晒得发白的公告栏上,我幼年画的小太阳还在歪着头笑。视频里推土机碾过菜畦的瞬间,邻居阿婆突然从镜头外递来沾着新泥的萝卜:"带着土才甜,城里的菜缺了地气。"
雨水惊醒了写字楼的绿萝,垂下的气根正在模仿爬山虎的走笔。当我用会议纪要折纸船放入马桶,漩涡中忽然浮现祠堂天井的四方星空。此刻故乡应是在落雪,那些轻盈的六角形结晶,是否正温柔地覆盖着童年刻在门楣上的身高刻度?
霓虹深处,总有青苔在空调排水管口悄然蔓生。就像我西装内衬永远别着的桃木扣——它来自老宅门前的春联钉,现在正替我收集所有城市星光,好在某个黎明将其锻造成带露的稻花。